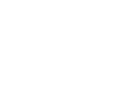《流沙刑》:直到法院判決有罪之前,任何人都是清白的
 2019-04-11
2019-04-11  2019-04-11 15:38
2019-04-11 15:38
事到臨頭,我的律師桑德看起來最漫不經心。「我站在妳這邊。」他只這樣說,擺出一副國字臉。桑德是那種喜怒不形於色的人;有他在,一切輕鬆自然,都在掌握之中。沒有情緒上的爆發,不表現情感,更不會笑到岔氣。他出生的時候,八成也沒有哭叫。
桑德和我老爸正好相反。老爸從來就不是什麼自己所希望成為的「酷男」(套他自己講的)。他睡覺時會磨牙,觀看國家隊的足球比賽時還會站起來。有次,鄰居在一週內停車停錯位置四次,老爸對著區公所辦公的迂腐老頭們大發雷霆;面對複雜難懂的電費合約與電話銷售員,他更會直接開罵。電腦、海關護照檢查站、爺爺、烤肉架、蚊子、人行道上沒鏟的積雪,排隊搭電梯的德國人和法國服務生,都是他痛罵的對象。任何事物都足以令他興奮,張嘴尖叫,猛力敲打門板,叫別人去死一死。相反地,桑德發怒的最明顯徵兆(或者說,從生氣轉為暴怒)只是皺皺眉頭,咂一下舌頭;這會兒,他的同事們就會驚慌大亂,開始結結巴巴,忙著搜找紙張、書本或其他他們覺得能讓他高興的東西。要是爸爸沒有氣急敗壞,反而冷靜、沉默下來,媽媽很可能也會有這種反應。
桑德從沒對我發過脾氣。對我所提的事情他從未感到激動;要是發現我說謊,或是我有所隱瞞,他也不會惱羞成怒。
「瑪雅,我站在妳這邊。」有時,他聽來比平常更累;但是,這樣就夠了。我們從來不提「真相」。
最主要的,我覺得桑德只在乎警方和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,是很聰明的做法。我不需要擔心他究竟是真想把工作做好,或者只是虛應故事。他彷彿只是把所有的死人、所有罪行和所有焦慮換算成數字; 如果等式不能成立,他就贏了。
也許,我們就該這樣做。一加一,不等於三。下一個問題,謝謝。
但是,這幫不了我什麼忙。一件事,要嘛就曾經發生過,要嘛完全沒發生過;就這麼簡單。其他那些拐彎抹角、旁敲側擊的花招,還不都是哲學家和(很顯然地)其他律師在玩的。還是那句老話:「事情沒那麼簡單……」
不過我記得,在那次到法院觀摩以前,克利斯特可真是堅持到底,使出渾身解數逼我們聽話。直到法院宣告判決,任何人都是清白的。他就把這行字寫在黑板上:法治基本原則。(薩米爾又點頭了)克利斯特要我們做筆記,抄下來。(雖然薩米爾根本不需要做筆記,他還是乖乖抄了。)
克利斯特喜歡用短句學到精華,然後反過來提出問題。兩週後我們測驗,一個正確的答案可以拿到兩分。為什麼不是一分?因為克利斯特認為,這種背誦式的習題還是有灰色地帶,你可以做到「幾乎答對」。一加一當然不等於三,但你既然還知道用數字作答—我就給你半分。
總之,克利斯特帶我們到法院觀摩,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了。瑟巴斯欽直到最後一年才加入我們班;他沒去那次觀摩,之後必須重新去一次。那時候,我在學校過得其實很愜意,和班上同學,以及從一年級以來各個不同的科任老師,都處得不錯。化學老師約拿,講話聲音有夠低,總是紀不起來學生叫什麼名字,等公車時,背包還低低垂到腹部。法文老師瑪莉.露易戴著眼鏡,頭髮髮型活像蒲公英,總是狂吸著一小片止咳藥,嘴巴噘得像小野莓一樣小。體育老師佛利格總是剪著小平頭,整個人看來宛如一塊剛上過亮光漆的木質甲板,性別不明,頸上掛著哨子,寬闊、閃亮的小腿刮得乾淨,身上總散發出毛圈襪和別人的汗臭味。頭髮漂白、心不在焉的莫琳則是數學老師,面帶不滿,經常遲到;她每週平均請兩天病假,臉書上的大頭照,擺著一張自己身著三點式比基尼泳裝,比現在年輕、體重至少少二十公斤的照片。
然後,就是這位克利斯特.史文生了。他非常投入,神情彷彿在說「來吧,我們就在瑪莉亞廣場見。現在,表決!」不過,他整個人卻像馬鈴薯泥拌奶油醬搭配炸肉排一樣平凡無奇。他以為搖滾音樂能讓世界免受戰亂、疾病與饑荒之苦;作為一個老師,他講話的聲音異常激動、投入。這種聲音唯一的用途,就是讓一條狗聽話,開始搖尾巴。
每天,克利斯特總會帶一整個真空瓶,裝著在家裡煮好的熱咖啡到學校來;咖啡裡加了許多牛奶和糖,活像流質的粉底霜。他把咖啡倒在自備的馬克杯(「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」)裡,將杯子帶進教室,還在上課時續杯。克利斯特喜歡規律:每天都做一樣的事,最喜歡的歌還要一放再放。想必他從十四歲以後,就每天吃一樣的早餐,某種長途滑雪時吃的玩意兒:燕麥粥加越橘果醬和優酪乳(「一天三餐,早餐最重要!」)。他每次和朋友(麻吉)碰面,想必都會喝啤酒與一點烈酒。每週五,他會和家人吃墨西哥玉米捲餅;有什麼大事值得慶祝的時候,他會和「老婆大人」一起上街角的披薩店(還會幫孩子準備繪圖紙和粉筆),共享一瓶店裡最具特色的招牌紅酒。克利斯特很沒想像力,總是參團出遊,食物裡從不加香菜,煎東西只用奶油。從一年級起,克利斯特就是我們的老師;每星期,他至少會抱怨一次天氣是多麼古怪(「現在真是季節不分了」)。每年深秋入冬,他總會抱怨街上的聖誕節招牌,怎麼越來越早掛出來(「夏季航班的渡輪一停駛,艦橋路上很快就會擺出美輪美奐的聖誕樹了。」)。
他會抱怨八卦晚報(「這種狗屎,怎麼會有人讀?」)和Strictly Come Dancing 舞蹈實境秀、瑞典歌謠祭、Paradise Hotel 實境秀(「這種垃圾,怎麼還有人想看?」)。他把我們的手機視為眼中釘、肉中刺(「你們是母牛嗎?聊天室整天叮噹響,你們乾脆把鈴鐺掛在脖子上好了……那些垃圾有什麼好玩的?」)。每次抱怨時,他看起來都非常怡然自得,覺得自己很年輕,很「酷」(對,不只我老爸會用這個字)。彷彿他能對我們說「該死的狗屎!」,就證明了自己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。
每喝完一杯咖啡,克利斯特就會把一小塊口含菸塞在上唇下方,把殘餘物放在一張小紙巾上,再將它們扔進垃圾桶。克利斯特非常講究秩序與規矩,就連用口含菸也不例外。
之後,在逃漏稅經濟犯的審判結束後,我們回到學校時,他顯得非常滿意。他覺得我們「表現很好」。克利斯特總是只感到「滿意」或「擔憂」,不會大喜過望,更不會暴跳如雷。每逢遇到背誦式習題,克利斯特總願意至少給半分。
克利斯特死時,姿勢差不多就像我妹妹蓮娜睡得最熟時的樣子:雙臂抱頭,膝蓋彎曲,身體低低地躺著。在救護車趕來以前,他就已經出血不止了;我也好奇,他的老婆和孩子們是否會覺得實情並不單純。由於法院仍沒表示我有罪,所以我是無罪的。
.png)
延伸閱讀:《安眠書店》:充滿上癮魔力的心理驚悚小說